- 如此我说
- 09/16/2025
刘嘉:警惕数字多巴胺上瘾——从韩国立法限制学生使用手机说起 | 如此我说
作者:刘嘉
智能终端本身并不是恶的,问题在于,当它们逐渐掌控了我们的欲望,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如何主动为它们设限,学会自我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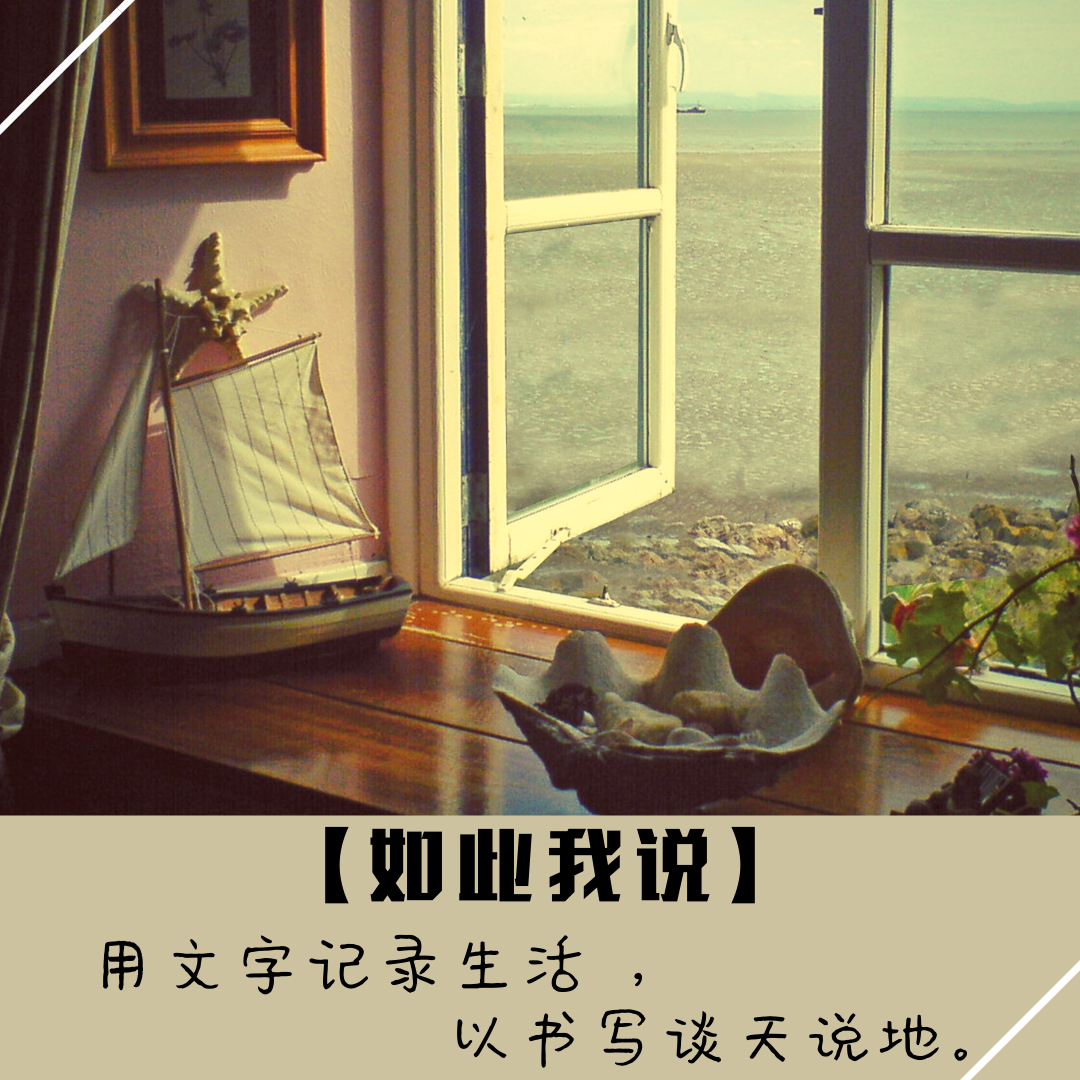

近几年,关于学生使用手机的讨论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升温。近日,韩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从2026年3月1日起,韩国全国小学生、中学生在课堂上将全面禁止使用手机和智能设备。
数据显示,韩国大约有四分之一人口存在过度依赖手机的情况,其中10至19岁青少年比例高达43%。大量家长反映,孩子们沉迷社交媒体,不仅影响学业,还干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流,甚至衍生出校园欺凌问题。教师们也有类似感受:课堂上频繁被手机干扰,严重时甚至引发学生与教师的冲突。

不仅韩国,美国、法国、葡萄牙、荷兰、芬兰等多国也陆续收紧校园手机使用规范。例如,美国德州自2025学年起全面禁止学生在上课日使用手机,部分州要求学校建立没收制度,确保学生无法在课堂与休息时间使用。法国自2018年起全面禁止15岁以下学生使用手机,强调此举有助于减少校园欺凌、提升专注力。
放眼国内,深圳近期的讨论也让人关注。一位深圳家长在人民网留言,建议禁止中小学生携带智能设备进入校园,担心这类设备分散注意力、影响视力和学习。当地教育局回应称,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相关规定,学校有权对智能终端产品进行管理,课堂上禁止使用,校内统一保管。部分学校通过开通班主任热线、设立校内电话等方式,兼顾学生与家长的联系需求。这一政策与韩国等国的做法在精神上有相似之处:核心目的都是保护孩子的学习环境、促进身心健康。
不止是一个技术管控问题
多项研究表明,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人的抑郁、焦虑、睡眠障碍乃至自我伤害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尤其是在大脑尚处于发育关键期的青少年阶段,神经可塑性强、情绪调节能力尚未成熟,过度使用手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和隐蔽。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太多具体的案例。我认识一名高一学生,入学后不久便迷上了手机游戏和短视频。原本成绩优异的他,逐渐在课堂上走神,作业拖延,经常熬夜刷屏。老师发现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出现自我封闭的倾向。随着社交媒体上的攀比和评论增多,他开始出现轻微的抑郁症状,家长不得不寻求心理咨询和专业干预。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城市中越来越普遍,显示出智能手机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延伸到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层面。
然而,限制甚至禁止手机使用远不止是一个技术管控问题,更触及社会文化机制与人性深层的挑战。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预言的:人类或许会沉溺于那些令人麻醉的愉悦工具,而如今的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平台,正成了这个时代的“数字多巴胺”(编注:digital dopamine. digital大陆地区译为数字,港台地区译为数位),无声无息地重塑着我们的认知和情感结构。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安娜·莱姆克(Anna Lembke)在《多巴胺国度》(Dopamine Nation)一书中指出,智能设备和社交媒体如同“数字注射器”,通过持续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将使用者推向难以自拔的成瘾状态。这种依赖不是因为内容本身有多吸引人,而在于一种被“未知的期待”牵引的心理机制。它与赌博成瘾的逻辑几乎相同:真正让人上瘾的,并不是赢钱的一刻,而是胜负未定时,那股刺激神经的多巴胺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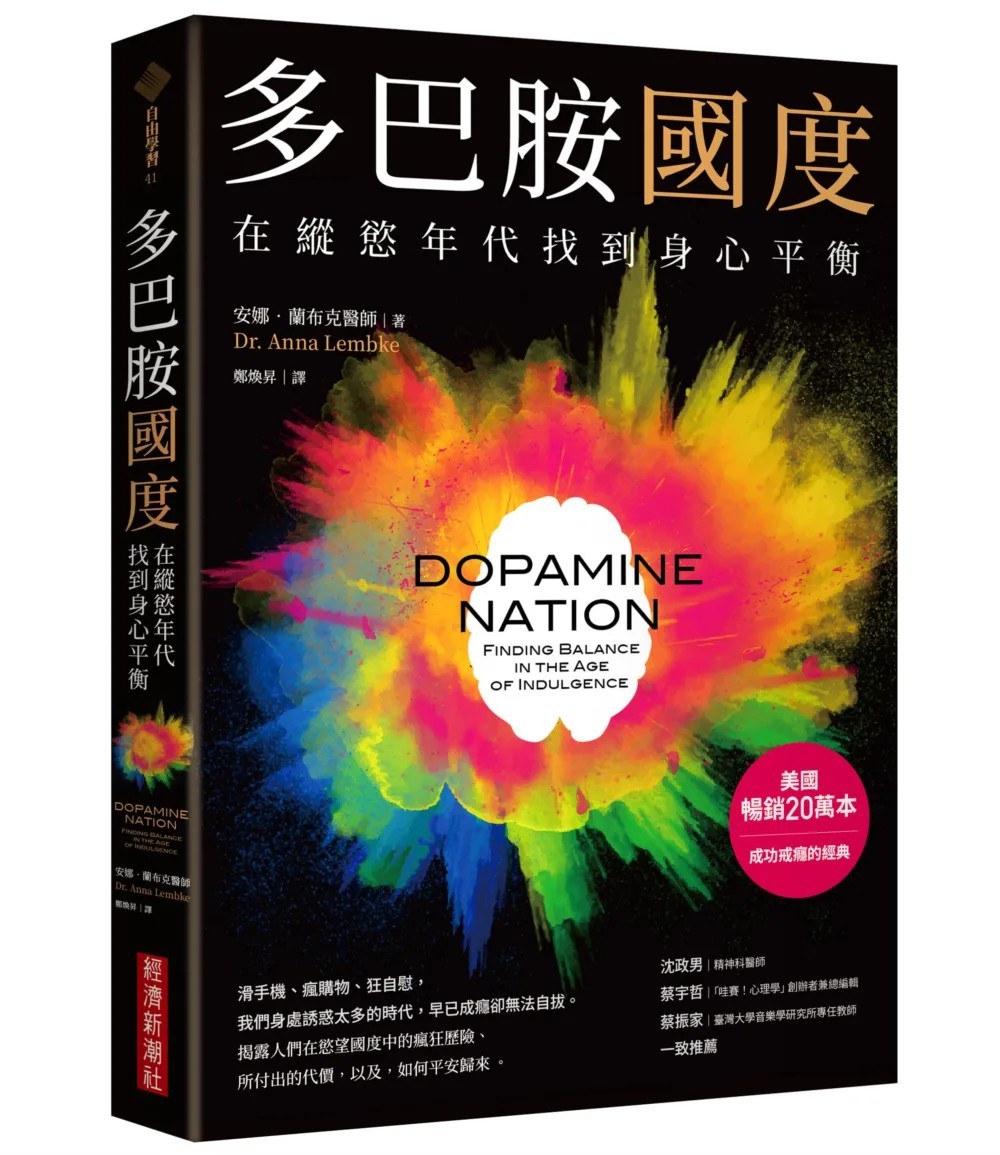
当我们无休止地刷屏、滑动,大脑在不断接收高频刺激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细腻感知。人际关系趋于浅表,专注力持续涣散,深度学习与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断被侵蚀。
爱应当有秩序
圣奥古斯丁曾指出,爱应当有秩序,人应当去爱那些该爱的,不应当过度偏爱不该过度热爱的事物。毫无疑问,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是一种“过度热爱”的诱惑。它占据了人的时间、心思,甚至情感,让人远离主、远离家人、远离真正的人际关系。我们若不谨慎,很容易在数字多巴胺的洪流中迷失,日常灵修和人际关怀被分散、削弱。
我们都体会过:一旦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浏览消息或刷短视频,便很容易陷入其中,仿佛被无形的漩涡卷走。原本清新的早晨,被碎片化的信息和不断跳动的通知所占据,一天的时间从一开始就被消耗殆尽,甚至一整天人都会思绪分散、心神疲惫。
智能手机的普及,也让青少年的阅读能力和专注力明显下降。属灵生命的成长,本应依赖耐心、安静和深思。然而,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的逻辑恰恰相反:它不断吸引注意力,让人不停滑动屏幕,被源源不断的新鲜内容牵引。久而久之,哪怕是一篇两千字的文章,也会让人觉得冗长、难以坚持。
这种习惯不仅影响学习和思维能力,也会侵蚀信仰的深度。当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信息摄取,思想和属灵生命也容易流于表面,缺乏扎实的根基。长此以往,我们在信仰上可能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层面,很难经历真正的生命成熟。
韩国的立法行动,实际上提醒我们:现代社会的便利与自由,并不总是人类心灵的福祉。限制手机使用,是一种保护,是为孩子建立清晰界限,让他们有机会在课堂上专注学习,在生活中体验真实互动,而不是被数字世界裹挟。对于我们成年人,也是一面镜子:若青少年需要被保护,我们自己更应学会自律,辨识哪些媒介和行为真正有益,哪些只是快速、短暂的满足,却会长期侵蚀我们的注意力与心灵。
所以我们当看到,限制手机的使用,不是剥夺自由,而是一种机会,给予我们选择、深思、专注的机会。课堂上没有手机,孩子们可以真正倾听老师讲解、与同学互动、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家庭中减少屏幕时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可以有更多真实的交流;个人生活中减少数字多巴胺刺激,我们可以重新体会到安静、默想、灵修的价值。
我越来越觉得,网络暴力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失去了“看见人”的能力。哲学家伊里斯·默多克曾说,道德生活的核心,不在重大抉择的时刻,而在日常细节中你如何去“看”别人。当我们真正看见一个人时,不是只看到他的标签、身份、过错,而是承认他是一个有尊严、有复杂情感的生命。
但现实是,我们更容易看见的,是“立场”“阵营”“群体身份”。当人被简化为一种身份或标签,他就不再是完整的“人”,只是一个“代表”,一个可以被攻击的符号。于是,当我们对着头像开火时,不会感到愧疚,因为那好像不是一个会受伤的人。这种“看不见”,不只发生在网络上,也发生在地铁里、餐馆里、办公室里。当我们对清洁工、快递员、服务员冷眼相对时,我们也是在忽略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爱人如己,不是浪漫的口号,而是一个极其现实的操练,当你在生活中真正遇到另一个人时,你要放下成见,用耐心和分辨力去看他。这种“看见”,可以很细微:在上网评论前,先问自己:“我看到的是全部事实吗?”当身边人情绪失落时,留意到他的沉默,轻声问一句:“你还好吗?”在公共争论里,试着先去理解对方的处境,而不是急着反驳。
选择去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学校以及身边的社群都可以成为我们重建生活秩序的支持力量。即便未来数字化会更加深入,我们依然要清醒地认识到:专注的能力、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内心的平静,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真正财富。因此,合理使用手机,不仅关乎孩子的成长,也关乎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如何守护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结。不妨借鉴一些可行的做法,比如在教室、办公室或书房中设立“无手机区”,让心灵有喘息之机,让思考重回深度,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被屏幕切割。
活在这样一个信息与诱惑无处不在的时代,学会认清什么是过量、什么是节制,已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课题。限制手机真的限制了我们的生活吗?当然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放弃某一种生活,实则是选择更真实、更专注,也更自由的生活。这的确像某种“舍己”;但只有相信它值得,改变才会发生。就像很多人明知锻炼辛苦,却仍坚持运动,因为他们明白,短暂的不适,换来的是长久的健康。
作为跟随者,我们注定要活出不一样的态度,哪怕是在屏幕使用上,也不盲目跟随世界的节奏。这需要我们主动愿意付出代价,做出不同的选择。离开了手机,效率或许偶尔降低,生活某些片刻也不再那么方便;但我却因此听见内心的安静,重新拾起书本,更专注地陪伴孩子成长。与人交谈时,我能放下设备,看着对方的眼睛;清晨醒来,我不会下意识地摸手机,而是会从容地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天。
我们感激科技带来的种种便捷,但当“便利”成为捆绑,我们或许更需要勇敢地拥抱一种“主动的不便”,世人以为限制自由的,其实是走向自由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