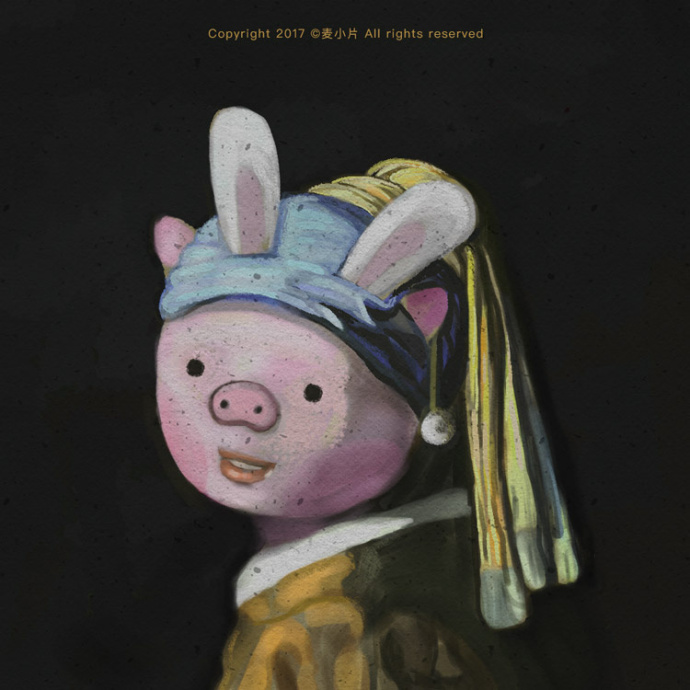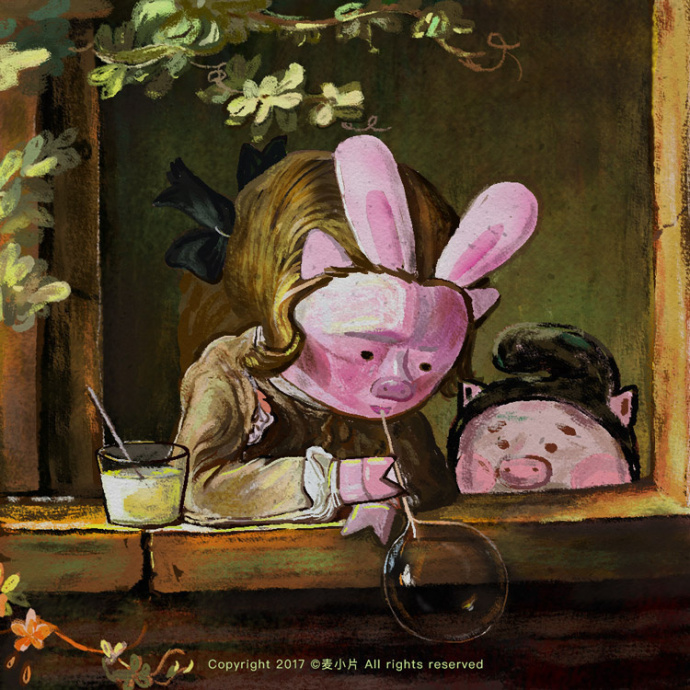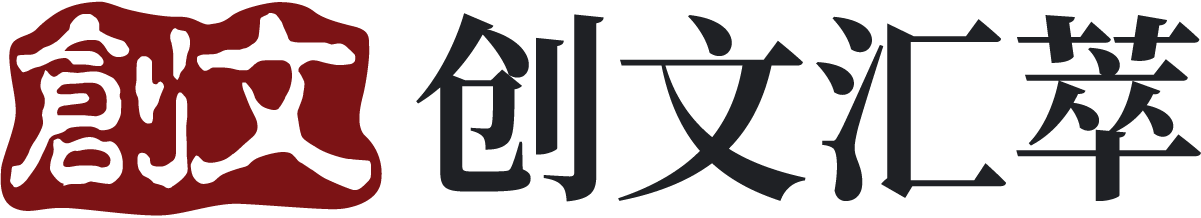很多人不太敢定位自己是文学创作者,也有人不了解自己可以成为文字事奉者,更不清楚创作者老实说并非天生,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到底有没有这一块。如果我们把文学艺术的创作者统称为艺术家,在身份中,其实最大分裂不在于谁是艺术家和谁不是,而在于谁了解自己有创造力和谁被说服自己没有创造力。最大分裂是在谁了解自己艺术家的天性,谁仍然无知或否定自己巧匠的灵魂。[Erwin Raphael McManus, The Artisan Soul, NY Harper Collins 2014, p4, 莫非译。]许多艺术家的传记也显示,通常都是创作者个人先认定自己是一名艺术家,然后再活出这样的身份,去创造一个生活来配合创作。我个人也是透过神的文字事奉呼召,先认定写作是我一生的命定,然后再发展出一种符合这写作呼召的生活方式,渐渐长成为一名创作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创作者,原因有下面几种:
人类是神按照祂自己的形象所造,而我们的神就是一位伟大的创作者。有位基督徒作家盖尔(Ken Gire)形容上帝的创造时,特别有着艺术情怀[Ken Gire, Windows of the Soul, Grand Rapids, Zondervan,1996 p16, 莫非譯。]:上帝展开了天宇,用印象派的星星点缀夜晚。把阳光设定为一天的节奏,月亮以月份的节奏,季节为一年的节奏。祂用风吹过芦苇沼泽,遥远的雷鸣轰轰击鼓。祂用一块黏土形塑一个像自己的形象,并吹进气息。另外又制作了一个对应的人来完成形象,并将两方融合在一起,置他们于创作的中心。在那里有诱惑,也有堕落,还有巨大的损失和隐藏。神寻找藏身的夫妇,把他们抱起、掸掉灰尘,再拉近。然而当时他们并不了解。之后,神搜寻他们的子子孙孙,并写下这搜寻的故事。在其中,上帝赐给我们艺术、音乐、雕刻、戏剧和文学。这些成为带领人类走出隐藏地方的路径,也成为引导我们寻找所失的路标。同时,用世间和天堂的一些东西所塑造出来的我们,常常会在两个世界中被撕裂。一方面我们渴望隐藏,一方面我们又渴望寻找。带着心头依稀记得的话语和灵魂中尚可辨认的草稿,我们有些人走出了隐藏之处开始寻找。
然而,除了专业创作者,很少人会看自己是有创意的艺术家。写《推拿》的毕飞宇在《小说课》中提到:我依然要强调,只要你热爱,用心,用脑子,再有一个好老师,你自己就有能力挖掘自己的天赋,会让自己的天赋最大化,这一点我一丝一毫不怀疑。我同样不怀疑的还有一条,你不用心,不用功,不思考,不感受,不训练,那你哪怕是莫言,最终也只能是闭嘴。[毕飞宇,小说课,台北九歌,2017,100页。]在文学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袪魅,不要刻意地神化天赋。神化天赋是一些人的虚荣心在闹鬼,别信。你们要相信我,天赋是可以发掘的,天赋也是可以生长的,直到你吓了自己一大跳。[同上。]毕飞宇口口声声说的“天赋”,就是在我们里面创作的天分。一个可能不认识神的中国作家,从自己的写作经验和观察中都可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基督徒如何可以忽视?
只是,很多时候艺术天性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组合里,却被后天教育给扼杀了,让我们失去创作的激情。也许你认识这样的人,他不见得拥有任何艺术形式的创作,但却可能常常在生活中“兴风作浪”,过着变化多端的创意生活。比如说我们家先生永浩从小喜欢音乐,但家里没有栽培的环境,因此最不花钱的唱歌成为他一辈子的热爱。教会诗班多年没有断过。儿子的成长环境自然比较有条件,因此他学琴考到最高级。之后,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用电脑录制CD,成为用音乐来写日记的音乐创作者。但那也只是玩票性质。而我,因为呼召而花了一生的力气,来开发自己写作的能力和恩赐,渐渐走上专业的写作。同一个家庭的三种状态,基本上涵盖三种艺术家状态:嗜好、玩票和专业。你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充满艺术家的家庭,或反过来说,每个家庭都有类似的状况,就看环境条件和个人性情。因此,创作者的身份会在某些人身上特别彰显,比如说米开朗琪罗会画西斯廷教堂、荷马会述说史诗故事、莎士比亚会创作剧本、大卫会弹奏十弦琴。我们每个人虽然都可以创作、揭露和诠释这个世界,但是有些人创意的恩赐和技巧就是会比一般人强一些。
如果说要像小孩一样方可进天国,是否在创作方面我们也要回归像小孩,有童心童趣才可能回复艺术家的身份?内里有创作渴望的人,一定要找回里面的艺术家身份,也要找回创作的热情。如此,才能为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找出一套表述的语言。这绝对不只是一个嗜好,在其中也有生命和灵魂连结的部分。文学艺术对信仰传递深具影响力,这点我们多少都可以感受得到。历代历史中,基督教的牧师、作家、教师、讲员,凡对当时世界大有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少数几位能影响当日未信世界的人,他们的影响力,从人的角度而言,无一不是由于能将艺术和理论做最佳结合的缘故。他们都是深沉的思想家,能以美妙、上口、易记的形式来说话、写作。[唐斯,预约心灵沃土,台北校园,2001,83页.]语言大部分的力量和说服力,是透过艺术而来,不是透过理论。换种方式来说,信息若没有被赋予艺术的成分,就没有能力说服人或改变人。[同上,88页。]在基督教各种形式的服事中,不论是传递异象或讲道、教导,文字装备绝对必不可少,它可以提升基督徒的表达能力和增加服事的影响力。《不再一样的领导力》(Spiritual Leader ship)一书的作者布克比(Henry Blackaby),提到属灵领袖也应该是语言和沟通的学生。虽然最有效沟通的关键是圣灵同在,但也不能否定领袖需要在语言技巧上钻研。在很多事工上,能几句话就搞定,一席之谈就定神国江山,是每位基督徒的梦。现实里,许多基督徒却常觉得自己语言无力,不管是神的信息,个人见证,或是简单地解释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有时费尽口舌也说不清楚。
除了祷告寻求和忠心准备,在服事里,我们缺的是语言呢?还是丰富的字汇?还是思路的条理?我们弱的是对会众的了解?对传递方式的掌握?还是对当代文化的抽离?写《领导智慧》(Leading Minds)一书的作者加德纳(Howard Gardner)观察到,大部分领袖都展现出一种“语言智力”,也就是用语言或文字来领导或说服的能力。但这种语言智力却并非每一位领袖都天生具有,可以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许多领导苦于驾驭不了语言,进而推动不了异象,苦口婆心说出来的道,却字字句句旁落,无法生出影响。在这方面,丘吉尔最清楚语言的力量。他知道如何善用文字可以影响民心,鼓动出征。他说:“我能奉献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这句话后来成为当代凝聚民心的一句名言。但是丘吉尔对语言的掌握能力却非天生,而是下过一番苦功琢磨的结果。他自幼口吃,年轻时便大量沉浸在经典文学名著中,包括莎士比亚剧和钦定版(King James)圣书。从阅读中,他培养出对文字的敏感,知道不是每个字都是一样的力道,有些文字或句法会在人心内燃起热情,在脑海里留下生动的图像。也因此他的用字遣词,具有高度诗意和小说想象,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和句子谈恋爱”。其实不只是对文字的敏感度,还有说故事的能力也至为重要。布克比说,传统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就是说故事。许多领袖书籍也都看重如何说故事,因此才会产生一个新名词:“故事力”。而且强调没有故事力,就没有感动力,故事力可以决定影响力。置入我们的服事中,异象是否可以传递得令人有如眼见?事工是否可以激励人投入?各样见证是否说得清楚神圣作为?都是基督徒的故事力有多少来定沟通成败。所以为了传福音,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在文字语言上涉猎和多面使用。如此说来,再问一次,你看自己是一名艺术家或创作者吗?你知道认定这身份后,生命就好似开了一道大门,从此可以走入什么样的丰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