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此我说
- 11/04/2025
【时评】细雪:两代女人的故事——我到底要过怎样的一生?
作者:细雪
电视剧《余生有涯》以女性视角直面性侵和两代女性不同抉择的话题。面对女儿被凌辱,母亲如何从极力打压女儿,走向认同、支持,最终达成两代人的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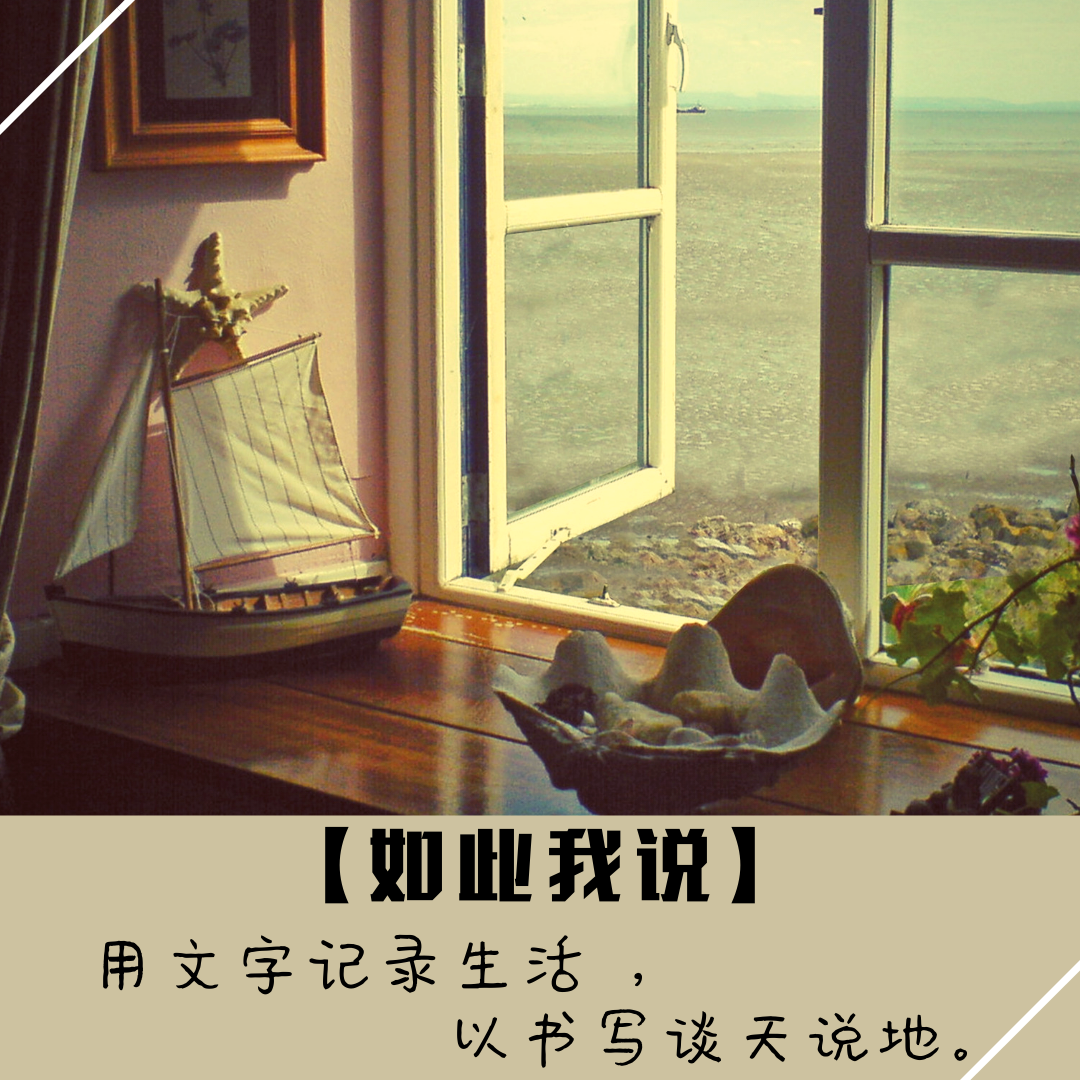

每个女人的一生都有故事。10月16日全国首播《余生有涯》,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勇敢直面性侵,用法律途径为自己讨回公道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牵扯出更广阔背景里,两代女人的故事。
她的名字叫黄桂芬
第一次出现她的时候,没有名字,没有画面,只有声音。
“念文(主角思北的弟弟)房子贷款申请还没下来吗?……”
手机上弹起一条信息,对方语音催促,夹杂着一种压迫感。接到类似的信息显然已经成为思北的生活常态。思北眼帘下垂,愁容爬上眉梢。
传来语音的是思北的母亲,黄桂芬。得知她的名字时,后知后觉——剧情推进了好久,从思北父亲的口中喊出。
她过的一生,如同名字一样,不常被提起,也很少人记住。提起她,便是叶家的媳妇、叶老师的妻子,是思北和念文的母亲……这是上一辈女人的常态。她把这样的常态活成理所当然,并且默认女儿也应当如此过一生。
我不想再用其他代名词框住这个女人,她有名字——黄桂芬。
她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面前,是女儿遭遇凌辱后,匆匆赶到。面对骤然降临的噩耗,她神情慌张中,强装镇定。“痛”这个字她或许选择刻意回避,尽量将它说得很轻,好似描得越轻,女儿越能相安无事,像她一样忍忍就这么过完一生。
面对不公,“报警”两个字从来没有出现在她的选项清单里。如同她的人生没有选择一样。
与其说她为思北做了选择,不如说她一直都是如此做选择。或者说,她应该如此选择。

不少网友谩骂黄桂芬,并且呼吁后面的剧情不要为她洗白。可是,看到这位面色憔悴,嘴唇白得发紫,白发稀疏的女人,我却恨不起来。
她,像极了我们生活里遇到的许多上一辈的女人。只是她把现实活成了一个缩影,以一种蛮横强势的姿态,逼着女儿像她一样,吞下所有苦水,咬着牙爬过去。
她心里痛过吗?我想是的。只是她不善于表达,正如过往的人生里,一次次面对打压和失去时一样。
很多人讨伐她重男轻女,宁愿给成绩平平的儿子择校费,也不愿给成绩优异的女儿学费。为了让女儿随时贴补弟弟,她到公司无理取闹,让女儿丢了工作,回到家乡沦为他人践踏的猎物。
可是,在后来她和思北的对谈中我们得知,黄桂芬何尝不是那个一直在退让弟弟的姐姐?
我并不是想将她的过错合理化,只是想探究一个女人的过去如何影响她的生活。很多时候,论断一个人的行为远比穿透一个人的灵魂容易得多。
记忆交错间,回到了她刚生下思北时,婆家人因为生的是女孩,丝毫不顾及她的感受,强行要求把孩子带到乡下去养,并且要求她辞掉工作,再生一个弟弟。那时的她强忍泪水,没有反抗,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咽。后来被发现超生,丈夫因此丢了工作,思北的存在仿佛成了她生活的累赘。
记忆大门打开的时候,婆家、丈夫、女儿、儿子多重否定的声音席卷而来。每一扇关系的门都紧紧关上,如同她和任何一层关系,都隔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一样。
当一幕幕“内情”摊开时,让人对这个强势到无可理喻的女人不禁发出一声声叹息。
叶思北:“不像你”是对你人生的否定
在28年的母女关系中,思北是迈出改变第一步的主动方。
和黄桂芬不一样的是,思北有名字,而且很响亮。年少时她的名字就记在光耀的品学兼优名册上,她也曾光彩照人地出现在领奖台上,还曾在全校师生面前发表励志演讲。
她坚信“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她努力过,认真过,也拼命过。她有和黄桂芬一样的韧性,只是她不把自己的人生赌在被藩篱禁锢的家庭。可惜她始终逃不过掌控,最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那一夜,前所未有的痛唤醒了她里面沉睡的真正自我。在秦南的陪伴下,她开始突破自己,改变与母亲长久以来相处的模式。
当她终于痛下决心选择报警,在医院长廊和母亲激烈对峙时,现实仿佛照见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不同的人生。一种是上一辈女人墨守成规地活在“应该的人生”里,另一种是下一代女人突破框架活在“想要的人生”里。
“我要报警。”思北一字一顿,铿锵有力。这次,她忠于内心的感受,不再委曲求全。“我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那场剧痛,使她穿过死亡之门,决心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她所要的公道,不只为那一夜的噩梦,还有过往28年来,因为她是女孩,在家庭里所遭受的一切不公。

报警后,面对黄桂芬指责不懂事,思北说出她眼中的母亲:“你是爱我的,我知道。你对我的爱和念文(弟弟)的不一样。你对我不光有爱,还有嫉妒。”思北很敏锐,一语戳破了黄桂芬内在的心理防线。
黄桂芬之所以活成一个空壳,并不是因为无能、无知、无感,而是为了假象的和平,刻意选择不去表达,久而久之,变得麻木,习以为常。
“你不能接受我不像你一样活着,因为这是在否定你的人生。”一直以来,她很清醒地看到妈妈的软肋,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思北曾和秦南说出对父母的感受:不是不爱,只是爱的不多。这句话道出了许多子女在与上一辈的关系里复杂挣扎的感受。
这些话就像刺一样扎进母亲的心,黄桂芬终于不再回避自己多年来对女儿的忽视。当叶思北走出内心的牢笼,与黄桂芬坦诚相见时,也迎来了母女关系的转机。
这一次离开是我的新生
往后的日子,黄桂芬渐渐转变了对女儿的态度,在一审出发前,她站在家门口陪女儿一起去;当思北在庭审外听了音频,受到刺激后,她用厉声斥责的方式重振女儿的信心,并给了她一个久违的拥抱;当女儿遭受流言蜚语,她挺身而出,不惜与人发生口角;当听到女儿在电视上被挑衅诽谤,她气得晕倒,被送往医院……
曾经想死死绑住思北的人生,按部就班地过一辈子,如今她却主动劝思北离开家乡,开启新生活。那些思北以为从不被在乎的时刻,照片、奖状……成长的记忆,却被珍藏在母亲的盒子里。思北眼眶泛泪。
母女最终和解。当黄桂芬用力摇动双手,脸上溢出少有的欣喜,眼神充满期盼,目送女儿离开南城时,遥想当年拼命拽住女儿回家乡的情景,眼前这一幕仿佛隔开了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人生。
如同叶思北的旁白:“我们母女都知道,这一次离开就是我的新生。这一生都不会像过去那样,让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交织成一张网困住自己。”
黄桂芬的一生,没有自己,被无形的枷锁困住。这个枷锁是传统、是习俗、是偏见……思北则选择了和黄桂芬不同的人生,不再被外在牢笼困住,与她的丈夫携手迎接新的生活。
“思北”这个名字是黄桂芬取的,寄托了对北方的思念。她的一生仿佛这个名字一样经过了寒冬冰霜。思北给未出生的女儿取名暖暖,仿佛期许着未来下一代的人生温暖向阳。
我越来越觉得,网络暴力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失去了“看见人”的能力。哲学家伊里斯·默多克曾说,道德生活的核心,不在重大抉择的时刻,而在日常细节中你如何去“看”别人。当我们真正看见一个人时,不是只看到他的标签、身份、过错,而是承认他是一个有尊严、有复杂情感的生命。
但现实是,我们更容易看见的,是“立场”“阵营”“群体身份”。当人被简化为一种身份或标签,他就不再是完整的“人”,只是一个“代表”,一个可以被攻击的符号。于是,当我们对着头像开火时,不会感到愧疚,因为那好像不是一个会受伤的人。这种“看不见”,不只发生在网络上,也发生在地铁里、餐馆里、办公室里。当我们对清洁工、快递员、服务员冷眼相对时,我们也是在忽略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爱人如己,不是浪漫的口号,而是一个极其现实的操练,当你在生活中真正遇到另一个人时,你要放下成见,用耐心和分辨力去看他。这种“看见”,可以很细微:在上网评论前,先问自己:“我看到的是全部事实吗?”当身边人情绪失落时,留意到他的沉默,轻声问一句:“你还好吗?”在公共争论里,试着先去理解对方的处境,而不是急着反驳。
我和母亲的故事:与永恒有关的梦
荧幕上黄桂芬和叶思北的不同人生——她们的爱恨交织,情感关系的变化成长——仿佛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现实中两代女人的模样。
我们或多或少会从这对母女身上看到现实的影子,从沉默、冲突到和解,在两代人不同的选择里看到了不同的价值观。
黄桂芬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缩影,折射出万千母亲的模样。我的母亲——一个很少喊痛叫累的女人,亦是如此。
自从父亲骤然离世,她独自撑起一个家。曾经青春时期于我而言是心灵的狂风暴雨,然而在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女性那里,成为无病呻吟。
从小到大的印象中,她像大树屹立不倒,用单薄的身子为我们挡住所有风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养活一家老小尚且不易,何况是失去了经济支柱的家庭?

和黄桂芬一样,母亲常常脱口而出“为你好”这三个字,成为我成长的紧箍咒。从小到大,身边所有人都告诉我:你妈妈不容易,长大后要好好孝敬。我曾像思北一样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有过和她相似辉煌的学生时期。
“报答”鞭策着我不能够懈怠,要足够优秀,才能够承载住厚重的母爱。我通过一切的努力要讨好,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家里,关于爸爸的离世,就像一个禁忌的秘密,不可奉告。成长记忆中,在和母亲的互动里,我几乎从来没有真实表达过。我怎能去向那个要报答一生恩情的至亲表达我的愤怒、哀伤?甚至开心都长着一张愧疚的脸,需要小心翼翼,偷偷藏进相册里。
在表面平静、内心躁动的青春期,每天夜里,昏黄的灯光下照出孤零零长长的身影,我站在家门口,目送母亲骑着自行车的背影离开,去到小姨偶然间调侃说的“新爸爸”家中,然后独自面对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而她从未向我提起任何和新爸有关的事,我也从未问过。
那没有好好为至亲离开哀悼伤逝过的童年,成年后,在心灵中刮起更大的狂风暴雨。它将我推入深渊的同时,却出乎意料地搭起了母女关系的桥梁。
母亲卸下了多年来坚硬的盔甲,为了爱向我俯身柔软下来。自此,她曾经贫瘠的关于内在感受的词汇,竟然在一夜之间迅速更新迭代:你心情好不好?你不开心吗?
我知道,这些词汇的背后是母亲心疼过后,生长出深沉有力的爱。它们唤醒了我麻木沉睡的灵魂,我开始认真审视二十几年来母女之间的关系。
很多亲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一旦定型,要寻求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往后,在和母亲相处时,我和思北一样开始划出界限。从曾经的隐忍沉默,到鼓起勇气表达真实想法的冲突,最终一步步和解。
很多年后,我有了和母亲一样的身份。那个夜晚,母亲向我讲述了当年医疗条件不发达,看着年幼感染麻疹的我日渐消瘦,她束手无策,只能坐在床上,和骨瘦如柴的我,面对面坐着对哭。
原来,母亲哭过,只是我不知道。那一刻,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掉落,仿佛思北看见母亲珍藏的盒子一般,我窥见了那些年我不曾知道的岁月,她所经历不为人知的艰辛。有一种莫名的情感涌流,后来我知道它的名字,叫做怜悯。
恍然明白:“母亲”并不是如思北口中用“好”或“坏”来区分或者混淆的定义;而是当恩典穿过信心的云层,每一个肉身之中的软弱个体,看到对方一生的全貌时,如同人子耶稣降卑,道成肉身,走进沾满污泥的罪人当中,用一生活出了怜悯的爱。
两年前,我开公众号下笔写文章,母亲成为我最忠实的读者。“妈妈鼓励女儿加油,以后成为一名作家!”当这句话从手机屏幕的对话框里跳出来,我哽咽着吃完那顿午饭。时至今日,她仍然身体力行地支持着我的写作。在过往三十多年的关系拔河中,我的母亲和黄桂芬一样最终带着深深的祝福,成为我面对往后人生的坚实后盾。
在两代女人的回溯中,我想过的这一生,不是黄桂芬“我应该”的一生,也不是叶思北“我想要”的一生,而是活在永恒梦里的一生。于是,我许下一个梦:
梦里,我和母亲双手合十,屈膝跪拜,用祈祷的嘴唇面向天上共同的父亲,将过往人生所有的酸涩化成恩典的甘甜,诉说与祂有关的故事!

